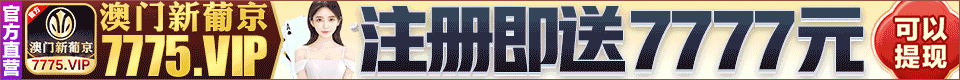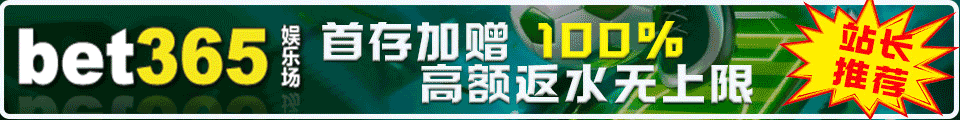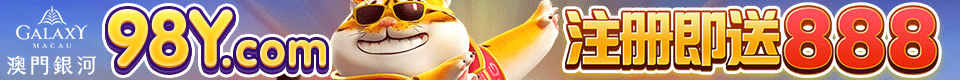女神彤
我是个保安。
每个月拿三千不到的工资,扣除生活费每月一千三百块,再扣除每月给上高中的妹妹生活费一千块,剩下的要死死攥在手里预防随时会来的战友同学结婚送礼。
在老家,我这岁数早该结婚了。很可惜我父母都没什么能耐,一辈子老老实实种庄稼,并没留给我什么可继承的东西——除了母亲去世前一场大病留下的欠债。所以我没有结婚的资格,只好安静地看周边同龄人一个又一个结婚…… 我上班的地方是一栋写字楼。里面总共驻了十三家公司,五家财务咨询,三家业务驻地办事处,两家婚介,一家婚庆礼仪,一家律师行和一家贵重金属投资有限公司。进出的人大都西装革履,门口经常停着宝马路虎保时捷法拉利。 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辆黄色的兰博基尼跑车。车主是个年轻人,二十六七岁的年纪,人长得很消瘦,头发微卷但是很蓬松,就像扣了一顶非常不协调的帽子在头上一样。不过这个人整栋楼都认识,他叫费凌,是五家财务公司里最大那家的总经理,那家公司是他父亲开的,他父亲是房地产商,听说家里资产有好几亿,城北福山花苑有一半是他家的。
其实他叫什么他多有钱根本不是我关心的事情,我不想拿他来衬托自己的人生是多么可悲,相比大多数的人来讲,我都是渺小至微不足道的,人和人没有可比性,我不愿意想这些给自己添堵。
我注意他,是因为一个女孩。
保安的工作很轻松,也很无聊。如果值夜班,就是件更加无聊的事情。通常到了下午五点以后,楼上就没多少人了,等过了九点,基本人去楼空,空荡荡的大楼里安静的像一座坟墓。我的同事小方是北方人,个子虽然高大,却是个很迷信的人,胆子尤其小,所以极其不愿意值夜班。我就私下和他调班,对我来说,白天或晚上上班没多大分别,相比白天的喧嚣,我更愿意在坟墓里独处。我们就这样形成了默契,好在这种默契并不妨碍到别人,自然也没人反对。
十点钟我会准时在楼里巡逻。坐电梯到顶楼,然后一层一层巡视到底层,确保大楼里已经没人在加班,然后检查一楼的门窗,最后从里面反锁卷闸门。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
当然不能睡觉,值班室是有监控的。
我有个便宜的山寨机,虽然外表不怎么漂亮,不过可以上网。
十一点三十分我会准时上厕所,我通常会去女厕,对于一个长期没机会接触女人的我来说,这种看上去很变态的行为也符合逻辑。
女厕很干净,和男厕一样大理石的地面,清洁得一尘不染的白色瓷砖墙面,马桶斜前方是洗手池,洗手池的上方有面用来整理仪表的镜子。我就坐在马桶上对着门口手淫。
我手淫的时候会幻想一些东西,有时候是一些回忆,有时候是发生在这栋大楼里的一些事情,当然都和女人有关。我坐的姿势有点怪,因为手部的前后动作需要,所以只能半个屁股坐在马桶的顶端,并且需要努力张开双腿防止精液喷射到鞋上。我之所以说担心鞋而不说担心裤子,是因为裤子一定要脱掉的,否则根本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一切。
手淫结束以后做一些简单的清理,回值班室给自己泡一包方便面,上面加一根一块五的香肠,以补充流失的蛋白质。
三点四十分,靠值班室窗外会准时有一辆卖早餐的推车,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开始炸油条蒸包子。背朝我做包子的女人长得并不漂亮,但肥大凸翘的臀部还是很有吸引力,尤其擀面皮的时候扭动,依然是我接下来无聊时间的的一项娱乐节目。这期间我会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们聊天,直到早起六点用普通的价格买一根特意为我定制的油条。
我每天的上班生活,就是这样。
前面说的那个女孩,名字大约是叫彤。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只听到一次有人在门口这么叫她。她叫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就像一朵花,开得正艳丽,你只需要安静地欣赏就好了。你可以闻到花香,看到风吹过她时的摇曳,和蜜蜂围绕她盘旋的过程。
只所以说过程,是因为蜜蜂从来不需要争取花的同意,他们天生就拥有这样的权力。对我而言,费凌就是这样的蜜蜂。
彤很年轻,带着些许学生特有的稚气,却屏蔽了学生的活泼。微翘的嘴唇永远紧绷,走路的时候下巴高高擡起,所以总给人一种骄傲的感觉。我觉得她骄傲一点也不奇怪,有些人,生下来就有骄傲的资本。
彤很会打扮,穿的衣服都很有品位,举止也优雅。她下班的时候通常我正在公司对面的巷子里吃饭,坐在临街的位置,可以远远望到她从里面走出来,挺着胸,下台阶时裙摆会轻快的飘动。于是我就常常选择在那个位置吃饭,不知道为了什么,通常我如果这么仔细看一个女人,就会在十一点三十分把她当作某种活动的工具。
彤是个例外。
她和我说过一句话。有次下了很大的雨,她站在门口等车,出租车只能停在人行道旁边,她就有些犹豫。我正巧打着伞从小吃店回来,就护她上车。从公司门口下台阶到出租车上,如果计算没有错误,应该用了六秒钟的时间,这六秒钟的时间里有四秒钟她和我贴得很近,可以清楚的感觉到彼此之间身体的摩擦,她的身体很香,那种香水的味道很特别,或许是带了春天雨水的味道吧?
她钻进出租车的时候因为弯腰的动作臀部碰了我一下。不轻不重,臀部的肌肉很柔软,像是汲满水的海绵,飞速地将我的裤子印湿了一片。然后她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谢谢。
我觉得她那句谢谢说得很真诚,或者她弯腰碰我大腿的动作是有意的,那是一种女孩非常矜持的暗示。我想她或许会在接下来的某天主动和我说话,像个很熟悉的朋友那样,随意的交换电话号码,然后会偶尔去一家对我来说比较奢侈的酒吧喝一杯,甚至有可能因为喝得太多需要我扶着她回家。
当然还可以有后续情节,不过无论剧情怎么发展最后我一定和她分开而且分开的理由一定是被隐瞒了的。
这只是我在那一刹那的假设。很快我就回到巷子里了,继续吃那碗剩下了一半的拉面。
据说有个关于拉面的笑话,甲对乙说,我会做拉面,我拉给你吃吧。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的拉面总有股笑话的味道。
此后的一个月零二十二天,我继续往常一样的生活,每天遥遥看着那道风景从门口掠过,然后飞舞着裙角隐去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直到下雨的那天。
确切地说,是那天的晚上十点五分。因为按照我的速度,刚好是巡逻到三楼那间办公室门口的时间。门是虚掩着的,所以我就进去了。
我知道那时候彤在里面,对于她是不是已经下班我一向很确定。
办公室没人,顺着几张办公桌的间隙过去,是总经理办公室。那间的门也开着一半,里面的灯光很柔和,人影绰绰约约夹杂着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我平静了下心情,慢慢走过去——如果没有意外,我能假装不知道她在里面,并且叮嘱一些走的时候关好门之类的职责所在可以讲并且不会让人意外的话。或者有更好的结果,显得十分随意的聊上几句。
然后我就看到彤坐在费凌腿上。
费凌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彤面向他很不雅观地骑在他身上,双手交叉从他脖子上绕过,她的头稍微有点儿歪,所以费凌可以清清楚楚从她的肩膀上看到我过来。
我很不想看到这种场面。偶尔遇到老板和秘书的这种暧昧,对我来说算不上意外,完全没有吃惊的必要。但我还是全身剧烈抖动了一下。
就在那个瞬间彤的身体也抖动了一下,好像冥冥中跟随了我的节奏,不同的是她还在继续抖动,虽然很缓慢,却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我承认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有些混乱,甚至忘记了脸上应该做出几分出惊讶的表情。
在我来不及做任何表情之前,费凌很坦然地贴着彤的耳朵说了一句话,声音不是很大,却刚好能被我听到。
他说:“你看,有人来了。”
彤没回头,只是很娇柔的“嗯”了一声,很明显的双手用力,使得自己的身体向上提起来,然后舒展地落下去,同时从鼻腔发出很享受的一种呻吟。
我这时候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
如果没有猜错,办公桌遮挡的部分对我一定是个打击。
我想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难看到暴露了我的一些隐私,这些隐私被费凌很敏感地捕捉到了。他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我,没有在提醒彤。而是用力推了一把桌子。那张办公椅就向后滑动了一些,把他们两个人的全身暴露在我视线里。 两个人的下体都是赤裸的。
端庄的职业套装裁剪很合体,从纤细的腰往下有一个自然的隆起,但是下面没了裙子,修长的腿在柔和的灯光下白得格外耀眼,浑圆的臀部在衣襟下隐现,不知羞耻的不断起伏。因为动作不太剧烈,臀部擡起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见一根水淋淋的男人阴茎偶尔闪现。
我也有这样一根阴茎,也可能比这个还要坚挺粗大,不过上面很少沾满湿淋淋的水渍,我是个注重清洁的男人。
我从来没机会看到她的这种动作,像一个没有廉耻的娼妇一样大喇喇坐在男人身上,下身套着一根男人勃起的东西。她还在继续动,节奏也在逐渐加快,长长的头发开始像波浪一样起伏,雪白的屁股撞击在大腿上发出轻微的响声,然后像皮球一样被迅速弹起,然后又重重落下去,长长的阴茎蛇一样被吞进里面。 费凌还在无声地笑,有些阴险和挑衅的意味。他的手环过彤的腰,掀开了她的衣襟,让两个人结合的部位完全展现在我的视线中。球形的两瓣屁股越来越快地跳跃,“啪啪”声音里夹杂了“咕唧咕唧”的动静,淫荡而放肆。
忽然彤全身颤抖了一下,然后发出一声尖锐的呻吟,如同撕裂了一块绸缎。紧跟着又连续哆嗦起来,电击一样不由自主摆动着身体。
我在A片中看到过这种情景。
费凌突然用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往后扯过去,紧接着右手一巴掌打在她脸上,喘息着叫:“骚货,别停。”
彤的身体似乎有些软,她勉强挺动着,精疲力竭的样子。可只要动作一慢下来费凌的巴掌就打过去,像抽打在马身上的皮鞭。
我觉得有些麻木,有什么东西被揪住了从身体里往外扯一样。
“趴到桌子上,我从后面搞一下。”男人扭转过彤,把她按在前面的办公桌上面。这时候彤才发现门口的我,惊叫着挣扎起来,努力摆动着屁股,想要避开费凌从后面抵过来的身体。但很快就被牢牢控制住了,那只手揪着她的头发将她的脸按在桌面上,很熟练地从后面插进去。紧跟着猛的一个挺身,重重地撞击在她翘起的屁股上面。
她的身体被撞得向前一冲,腰就塌下去,显得屁股翘得更高,身体被迫拧成了一段弯曲的S线条。
“看我搞女人兴奋不?”这句话明显是向我说的。费凌咬着牙继续干,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曲狰狞。身下的彤两腿有点站不稳,身子开始往下滑,一直滑到半身全贴在了桌面上。
她的眼睛眯起来不看我,沉重的鼻息被撞击的散乱短促,可表情却没有痛苦的意思,细白的手掌扒住了桌子的边角。
这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她没有求救,如果她求我救她,我一定会毫不犹豫上去把那个男人拎走,就算因为这样我丢了工作,被人狗一样追打。
费凌边搞边看我,忽然扯开了彤的上衣,把乳罩从下面推上去,然后攥住一边的乳房,一边捏着玩弄一边用调笑的口吻对我说:“你摸过她的奶子没?你看这奶子很挺很滑的,过来摸一把不?”
我攥着拳头,好像那雪白挺拔的奶子已经在我手里。其实我一定很想去的,我下面的阴茎已经很硬了,在裤裆里支起来,随便谁看一眼都会明白里面是什么情况。但是我走不动,也说不出话,傻子一样被那个男人调戏,不知道逃走,也不知道反击。
这时候彤呻吟着叫了一句:“我不要他碰我。”
我忽然间像个冰人被投入到火焰当中,能感觉自己被瞬间融化掉,巨大的挫败感被火焰灼烫焚烧|烧成了羞耻。
“为什么不给他碰?”费凌边干她边问:“因为他是保安?不配你?你不就是个骚货吗?你看自己现在这样子,淫荡的和妓女有什么区别?你看看他的裤裆支了那么高,肯定家伙也不小,干起来你一定很爽。”
说着从彤后面拔出阴茎,把她的扯到桌边,然后将沾满淫液的阴茎塞进她嘴里。接着擡手在她屁股上拍了几巴掌,说:“来吧,屄洞给你腾出来了。” 我终于过去了。
彤的屁股翘在我面前,阴唇湿淋淋的一片狼藉,刚被插过的屄洞还没合拢,阴道口的肉芽还在随着她的挣扎蠕动。
这个身体曾经是我不敢想象的,白嫩光滑,鲜活水嫩,被鱼钩吊住的鱼一样翻转腾挪着。
我机械地脱掉自己的裤子,阴茎很坚硬,光滑的龟头上溢出一点液体,我扶着它靠近那对雪白的屁股,然后按着龟头塞进一片细软湿滑的肉洞里。彤的身体颤抖着叫了一声,却因为口中有费凌的阴茎变得有些含煳。我在那声不甘心地叫喊里开始耸动,低头看自己的阴茎在她身体里进进出出,淫秽的液体被抽插出泡沫,堆积在阴唇周围,像一个拙劣的鸟儿筑起的巢窝。
彤的水又流了很多,腰不停地扭动,她的头靠在桌边,绯红的脸鼓囊囊涨起来,费凌的阴茎在里面,还在不断抽搐,戳得她发出“唔唔唔唔”的呻吟。 我快射精了,快了。
有一滴液体忽然落在她颤动的臀上,晶莹剔透,好像清晨的露珠。
我装做贪婪地亲吻她的屁股,把那滴露水舔进嘴里
相关推荐